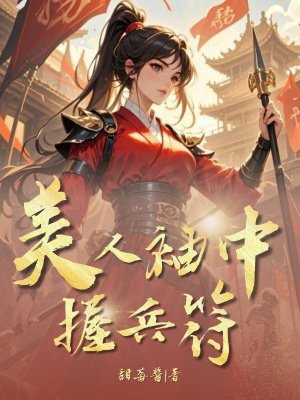首发:~一
她没有听到阿苏勒的回答,愣了一下扭头看去,看见外面又开始下雪了,年轻的大那颜默默地掀起帘子走了出去。
“你在东陆是不是又一次热血上涌?”大合萨严肃起来。
在法场上,自己岂不正像一个嗜血的魔鬼?阿苏勒微微打了个哆嗦。
阿苏勒揭开帐篷帘子,那一瞬间,他愣住了。帐外是一片看不到边的白雪,贴着帐篷一个女人蹲在地下,捧着一个铜盆,里面是喷香的獭子肉盖饭。那个女人双肩耸动,无声地哭泣着,泪水滴在她自己亲手烹制的獭子肉上。阿苏勒从她的背影里感觉到一股足以吞噬掉他的悲伤,他的身体在寒风里一寸一寸地冷却。
距离那顶白帐还有十几步路的时候,他听见了笛声,于是停下了。他太熟悉那笛子的声音了,听着就让人想到月夜之下女孩一个人脉脉低语,因为苏玛不会说话,所以她才会用笛子去表达。他的神思追着那旋律走,想着有几分腐儒气的百里煜认真地对他说,“尘少主吹的,是亲情啊。好像草原一望无际,亲人远行,吹笛的人留在帐篷外,看着风吹草低,等着那人回归,所以曲调始终低转。偶尔风来,看见远方的牧人马群,迎上去,却不是,于是又只有风声,仍旧是依依相望,只是多了几分失落。”
“你的爷爷其实是个怀有爱心的人,他年少时候远比我们青阳的先祖依马德正直。可他也未能逃过狂血的诅咒,他第一次爆发狂血,是因为当时掌权的青阳五大老密谋杀死了他的母亲,那一次你的爷爷独自杀死了数百人。他沉迷于那种力量,向人夸耀,自命为武神的使者,却不顾自己的性格越来越暴戾。最后他渐渐地疯狂了,怀疑一切,甚至怀疑他最心爱的女人,你的奶奶豁兰八失大阏氏阿钦莫图和人通奸,疑心你的父亲不是他的骨肉。于是他放逐了妻子和儿子,你的奶奶因此而死。你爷爷在清醒的时候想起这件事就会悲痛得吼叫,所以他越来越迷恋狂血上涌时候忘记一切的感觉,发起了很多战争。你的姑姑嫁给了真颜部的主君,本来是你爷爷最心爱的女儿,可她救了你父亲之后千里迢迢来北都城为他央求,你爷爷却不能控制自己,用鞭子勒死了她……”
“木黎将军……”阿苏勒的声音颤抖。
“我明白!”阿苏勒睁开眼睛,缓缓地点头。
阿苏勒沿着那条分叉的路慢慢地前行,雪飘在他的头发上,天地苍茫。他走出了很远,回过头,看见自己留下一串足迹慢慢又被新下的雪盖上了,远处两座白帐在雪里模糊起来,像是一座城门。他用靴子把周围的雪扫开,发觉自己正站在那个分岔口上。他看着脚下,想了想,走上了去另一边白帐的路。
旭达汗旁边的贵木一直低着头,此刻眼睛里凶光一闪,伸手就摸刀柄。旭达汗看着地面,默默地伸手把贵木的刀柄扣住。他没有再辩驳,帐篷里也就此沉寂下去。
阿苏勒被那个伴当引着往金帐后走去,这里是他从小熟悉的地方。蛮族把大君的整片营帐叫做斡尔朵,里面住着伺候大君的女人们和伺候的奴仆,差不多等若东陆皇帝的后宫。他放眼眺望,不禁愣了一下,在雪地里,他看到了两座一模一样的白色帐篷。在蛮族,大君的妻子们也被称为斡尔朵的女主人,其中又以大阏氏和侧阏氏为正妻,好比东陆的皇后和贵妃,只有她们生下的孩子才是嫡出,才可以作为继承人。大阏氏所居的帐篷是红顶,侧阏氏所居的是白顶,阿苏勒的母亲勒摩·斡尔寒就一直住在白帐里,可他站在岔道口,看着左右两条路,不知道往哪边走才对。
比莫干从黄金宝座上站了起来,走到人群中,摊开手,缓缓坐在地上,“我们这里有人的意见不同,那就按照逊王的办法,开一个小的库里格大会。大家都坐下发言,谁都能说话,谁也不要怀疑别人有没有说话的资格,都把心里的疑虑说出来。”
斡赤斤家主人摇了摇头,冷冷地说,“大君,我恐怕我的想法和您不同。将军们中主战的多,各家主人要和谈的多,这些都说明白了。我刚才说将军们没资格说话,并不是怀疑将军们的勇敢和忠诚。但我不得不说将军们靠的是勇气和战功,我们几个老家伙年轻时候也一样敬仰勇士,自己手里的刀剑也不含糊,可是我们如今管着自己家族下面几万人口,我们不能拿着大家的命去赌。这事情关系到北都城里几十万人的死活,将军们还要说什么祖宗的尊严不能让朔北人玷污了,祖宗的土地不能送给狼崽子,我不能同意。”
大合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每一次你使用狂血,这诅咒都会侵蚀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又远不如常人强壮。我听巴夯说了战场上的情景。那些东陆人当时用了某种秘术强行克制你血液里的烈性,秘术我懂得有限,可是越是强大的秘术越是危险,要压服狂血的秘术更是非常危险,就像东陆卖艺人玩的走钢丝一样,稍有不慎就会反噬自身。同是这些东陆人,他们的力量可能解开他们当时封入你身体里的禁制。你已经被这力量侵入了一次,所以连续一个月昏迷不醒,你要千万记住,无论如何,离那些东陆人越远越好!”
“不还是我说的那句?”巴扎捂着嘴笑了一声。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狂血往往会造就一个草原上的武神,然后彻底地毁掉他。至今以来所有拥有狂血的人,随着他们一再地使用这禁忌的力量,他们就会慢慢地丧失本性。你的祖先依马德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狂战士,他最后疯了,逼迫那些被自己霸占的亲姐妹和他彻夜狂欢后一个个咬死了她们,然后用刀一片片把自己的肌肉割了下来。”
脱克勒家族的主人翻了翻眼睛,以极度的轻蔑瞟了旭达汗一眼,“流着狼血的人就别多说什么了。”
他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总是在午夜醒来的时候听到笛声,那时候苏玛在外面,他在里面,只要他咳嗽一声,苏玛就会走进来摸摸他的头,帮他盖好被子。他倒从没有想过会是他在外面听,苏玛在帐篷里面。
“最大的……心愿?”阿苏勒记忆深处,慢慢浮起那个眼中有一道白翳的男人的脸。他叮嘱自己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来着,“去东陆吧!我的儿子,阿爸和阿妈会想着你。你回来的那一天,阿爸会带着你阿妈,带着虎豹骑的千人队,去天拓海峡边,看着载着你的大船乘风破浪地回来。那时候阿爸扶你坐在金帐里,你是新的大君,让草原上的人都叫你长生王!”在南淮的时间里,阿苏勒一直觉得这句话只是个空洞的鼓励,也从没有寄望父亲真的把大君的位置从矫健的哥哥们手里抢出来交给他。可是父亲说这话的时候,那双眼睛是那么的真诚和热切,热切得不像他自己。
莫速尔家的父子正拍着自己的肩膀互相埋怨对方的莽撞,看见阿苏勒慢慢从床上爬了起来,他们赶快过去按住了他。
“老死的,走得很安静。”年轻女奴说。
他忽地想起来了,这是木黎的家,他已经回到了北都城。他小时候跟木黎学刀,有时候太晚了,或者累得虚脱了,英氏夫人就把他带到自己的帐篷里睡,醒来就看见这根搓花绳子和铜铃,十年过去了就没变过,连那股羊奶的香味都一模一样。
“长……生王。”阿苏勒喃喃地说。
斑猫站住了,回头看着阿苏勒,不知道这个陌生人为什么知道它的名字。趁这个机会大合萨跳过斑猫,把巴呆抓了塞回自己的羊皮袍子里。
金帐里,比莫干、将军们、大家族的主人们都在。
阿苏勒呆了许久,默默地点头。
他忽然想要用力拥抱什么人,于是扑进去紧紧抱住了母亲。他的眼泪无法控制地流了下来,他把头顶在母亲的胸口,希望她能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怀抱。
比莫干遥遥地挥手阻止了他,“阿苏勒你不必跪,你醒来我很欣慰。你上阵很勇敢,我也很高兴。没事就好,去见见你母亲吧,她应该很想你才对。”
巴夯愣了一下,两个胳膊肘分别顶着两个儿子的腰眼,像只蛮横的野猪把他们拱开,“父亲在的时候,父亲先说话!”
“大合萨,我没事。”阿苏勒说。
他在帐篷外站了一会儿,直到笛声渐渐淡去,他才转身离开。
比莫干紧紧地皱眉,摇了摇头。铁由急忙上去斡旋,“现在大敌当前,我们有话好好说,朔北人可巴不得我们不信任自己人呢!”
“大那颜,真的醒了啊,这个月可吓死我们了。大合萨说你今天会醒,我就一直眼巴巴地看着,居然就让他说对了。”英氏夫人眼角里流露出笑意,和阿苏勒记忆中的一样,她从不是那种溺爱孩子的女人,可是她那带着英气的笑却能让她身边的每个孩子觉得她是最可依靠的姆妈。
阿苏勒的肚子很不争气地发出了咕咕的空响,仿佛是对英氏夫人的回答。阿苏勒愣了一下,抓了抓头。
“人的强壮,并不只是力气大,”大合萨指着自己的心口,“人的强壮,是在这里。阿苏勒,你明白么?你从不仇恨任何人,这不是你的虚弱,是你的强大。如果要克制那恶魔一样的血统,我们需要的难道不正是内心最强壮的人么?这是为什么你父亲要送你去南淮的原因啊,你父亲要你远离兄弟间的战场,去为他完成最大的心愿。”
大合萨犹豫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离开的时候你太小,老大君不愿意告诉你,怕你不懂,怕你害怕。等你回来,老大君都不在了,就让我这个老头子跟你说吧。你的病并没有被治好……其实你根本没有病,你的血统和普通人不同,你有青铜之血!”
他支撑着身体要坐起来,却被一只柔软的手按住了额头。他看过去看见了一张女人的脸,有些英丽威武,又有些温柔,十年过去居然只是多了几道皱纹,一样就能认得出来。
“哦哦哦,不过外面冷得很,就在帐篷里解也很好,一会儿让奴隶盖层土就好。”巴夯说。
阿苏勒愣了一下,不知该说感谢还是其他什么,刚一抬头,看见比莫干已经起身走了。他看着比莫干的背影,心里有些难过,他想自己大概是个多余的人,站在空荡荡的金帐里显得那么突兀。
“家父已经过世十二年了,”那个老头子说,“我幼时家贫无财,父亲为我手植梧桐,夏天在树荫下读书,父亲为我打扇去赶蚊蝇。父亲说,此树快长快长,我儿快长快长。这树亭亭如盖的时候,我儿也一定出相入将,车上翠葆霓旌。”
“拔都儿!拔都儿!”阿苏勒急忙喊那只斑猫的小名。
帐篷帘子被人一把掀开,一个闪亮的光头出现,冲进来的人急切得像只捕猎的斑猫,上去挤开英氏夫人一把抓住阿苏勒的肩膀,上下左右地看。
十二月十七,北都城。
巴赫慢慢抬起眼睛,“我们在谈的,是青阳的存亡,不是斡赤斤家的存亡!”
“呼玛呢?”阿苏勒随口问。呼玛是他母亲身边最得力的女奴,他有点想见她。
比莫干的一个伴当进帐来,“大君,阿苏勒大那颜醒了,正在金帐外等着觐见呢。”
“这里就你一个伺候么?”阿苏勒淡淡地跟她搭话。
“我怎么会那么久不醒?”阿苏勒问,“我并没有觉得很难受。”
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梦,梦有一生那么长,梦里他还在南淮,水波潋滟,他、羽然和姬野划着偷来的筏子在凤凰池上漂过。他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脑海里一片空白,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那么熟悉,似乎很久很久以前他就躺在这里,看着那个搓花绳子和小铜铃,听着它叮叮地响。
英氏夫人听得一阵心酸,上去抚摸他的头发,挥手让大合萨不要说下去了。
比莫干点了点头,起身说,“那今日先这样,这个小库里格大会我还要开下去,大家各自回帐篷去想清楚,我会再召集大家来。最后一件事,我知道城里有饿死奴隶的事情,我知道大家剩下的粮食都不多,但是奴隶也是人,得活命。尤其现在又是需要人的时候。”
他走上去,蹲下来,抱住英氏夫人的肩膀,低声说,“姆妈,有我啊……就跟木黎将军在的时候一样!”
“苏玛,这些年你过得好么?”他用极轻的声音对雪说。